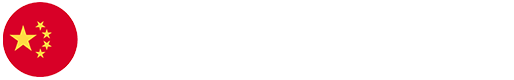早在本世纪初国会投票决定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制造商就做好了廉价商品开始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港口的准备。
然而,现实远超预期。从1999年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几乎增长了两倍,而美国工厂由于工资水平较高且安全标准更为严格,无法与之竞争。接下来,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冲击”摧毁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给从密歇根州到密西西比州的社区都留下了持久的创伤。
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来说,这些岗位的流失正是数十年错误贸易政策的活教材,他承诺,自己所推行的关税政策将有助于扭转这种损害。上周三,他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远超100%,尽管同时他也暂缓了对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巨额关税。
试图让制造业工作岗位全面回到美国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多少经济学家的认可。更鲜有人相信关税能有效达成这一目标。
研究该议题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特朗普误解了“中国冲击”的本质。他们说,这场危机的真正教训并非关于贸易本身,而在于揭示了快速的经济变化对劳动者与社区带来的沉重代价。若是未能理解这一点,特朗普或将重蹈其声称要纠正的覆辙。
重新审视历史遗产
关于“中国冲击”,首先需要明白的是,本文开头的叙述几乎每一部分都是经过了简单化的概括。
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几十年里,制造业岗位在就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左右开始,这种下降确实在加速了,尤其是在服装和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并非所有的下降都可以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或者更宽泛地说,并非都是美国的贸易政策所致。
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工厂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经济学家对各因素的权重存有争议,但无人否认:即便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也不可能维持2000年那样50万服装工人的规模。2016年首次提出“中国冲击”这个概念的研究论文也承认,在12年观察期内,中国进口仅占500万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一小部分。
“中国冲击”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代价格外高昂——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在19世纪初就认识到贸易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的道理。它的不同在于岗位流失的速度之快和集中程度之高。
短短几年内,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社区经历了就业岗位的蒸发。2000年,北卡罗来纳州希科里市的家具行业雇佣了超过3.2万名员工,占当地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十年后这一数字锐减60%,而类似的毁灭性打击在多地上演。
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受到这些岗位流失冲击的人群和地区应该能够相对迅速地适应。投资者本应廉价抢购那些被废弃的工厂和厂房,并为它们找到更具生产效益的用途。而失业的工人本应学习新技能,进入那些增长更快的行业,或迁徙至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新兴的高薪产业确实兴起,却并非出现在那些受制造业岗位流失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失业工人们不愿或无力迁徙寻找机会,只能留在社区艰难竞争寥寥无几的优质岗位,而这些岗位大多要求具备大学学历。
结果却是,他们进入了收入较低的服务性行业,薪资与之前在工厂的工作无法相提并论,或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男性的就业率断崖式下降,药物成瘾与早逝率激增。
因此,有关“中国冲击”的研究文献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变化本就艰难,骤变更是如此。
当产业更替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工人与社区尚能渐进调整。地方政府可培育新产业,父母引导子女选择不同职业。但当全行业在短时间内崩溃时,这套渐进适应的机制便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