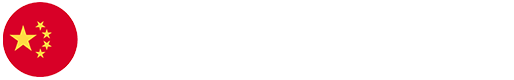朱莉娅·孙(音)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法学院学生,10岁之前生活在上海。去年,她在离校园不到一公里的一家亚洲超市购物时,零食区的一个包装让她眼前一亮。
“那是一种华夫饼干,我二年级的时候吃过,”朱莉娅·孙说。她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饼干了,还以为它早就停产了。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她说。
对于厄巴纳市和香槟市的6000多名中国学生来说,丰富的家乡特产和菜肴让这两座城市仿佛成了从伊利诺伊州中部平原上升起的一场“海市蜃楼”。
这两座城市被绵延数公里平坦的、绿油油的大豆田和谷物田环绕,总人口约12.7万,天际线最高的建筑也很少超过15层。这一地区并非人们印象中的大都会中心,按理说,想吃到地道的中餐,这里绝不会是首选之地。
然而,从大学主校区出发,步行一小段路,你就能坐下来享用一顿正宗的川味麻辣牛蛙火锅,汤底里满是青花椒。附近还有一家餐馆供应羊肉泡馍——这是陕西的一道羊肉汤,里面漂着掰碎的馍,是西安人喜爱的美食。如果深夜突然想吃长沙风味的臭豆腐,晚上8点半之后也能吃到,厨师会把炸好的黑色发酵豆腐块淋上亮晶晶的橙色辣椒油,和湖南省会街头小贩的做法一模一样。
在200公里外的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你得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到这样的菜肴,但在香槟市和厄巴纳市,它们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校园附近聚集了至少20多家中餐馆、面包店、珍珠奶茶店和亚洲超市。在香槟市被称为“校园镇”的主要商业街格林街,短短五个街区的范围内,橱窗海报和人行道上的夹板广告牌上满是饺子、面条和炒菜的大幅彩色照片,配有中文说明,通常也会有英文(但并不是都有)。
这些店大多是今年来新开的,历史几乎都不会超过15年。石黛(音)是当地的一名甜点师,老家在福州,她2010年第一次来到香槟市,当时她父母在这里开了一家中餐馆。她说,那时候竞争对手寥寥无几。
那时约有1100名中国学生就读于这所大学。如今,中国学生的数量是当时的五倍多,校园周边也成了草原上的一个小小唐人街。
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在美国各高校中位居第一。但根据《纽约时报》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2023年签证数据的分析,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南加州大学几乎并列第二。
国际学生数量的激增改变了许多地方的当地文化和经济,厄巴纳和香槟市并非个例。但这一地区地处乡村、相对偏僻,且中国学生数量异常庞大,使其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鲜明例证。
未来数月或数年,这里或许还会成为一个实验室,可以用来观察特朗普政府削减研究预算、收紧留学生签证(尤其是中国学生)所带来的影响。
玉米地里的盛宴
中国的大学生们给伊利诺伊大学起了个昵称——“玉米地”。这所大学因其周边的农田,以及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STEM领域的实力而闻名,而不是因为它附近可以吃到北方风味的爆猪肚。每年8月,数以百计新来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完全没想到这片“玉米地”里竟有他们从小吃到大的食物。
学校的招生人员偶尔会用饺子之类的美食来吸引潜在的学生。“我申请的时候,和导师Zoom视频了两次,每次他都告诉我,‘这里的中餐太棒了,你一定会喜欢的’,”来自上海、正在该校吉斯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斯嘉丽·钱(音)说。
6月,我和钱女士以及她的两位华裔同学在她们最喜欢的格林街餐厅“北味轩”共进晚餐。我们很快就落座了,她们说,这在学年期间很难得,这样的时候,门口几乎总是排着队。
北味轩是两年前开业的,店内铺着青灰色地砖,摆放着中世纪现代风格的家具,餐桌上方悬挂着石墨色的吊灯。在这样的光线下,拍出来的菜肴照片清晰,很适合发社交媒体,比如哈尔滨特色菜锅包肉:猪肉条经过两次油炸,形成浅金色的外壳,里面布满细小的气穴,裹上近乎透明的糖醋汁也不会变软。
“这和我在国内吃的很像,”在山东长大的李轩逸(音)说。
去年,有超过2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为他们服务的餐馆代表了美国中餐业的新浪潮。20年前在曼哈顿,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周边的街区几乎没有像样的中餐,现在已经成为上海醉蟹和港式叉烧包的宝地。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和艾奥瓦城的大学校园附近甚至也能吃到高水平的中餐。
与20世纪初为广东移民提供家常菜、铺着油毡地板的旧城区唐人街餐馆相比,这些新餐馆更具国际化气息;与20世纪60至70年代因躲避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厨师经营的贵族式中餐厅相比,这些新餐馆更加与时俱进。它们面向的是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顾客,往往氛围轻松、价格适中(虽然并非极低),且忠实地再现了真正的地方菜系。
香槟分校的学生们会在小红书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中文群聊里交流各地菜肴的信息。在这片“玉米地”点餐时,最有用的工具是亚洲外卖应用“熊猫外卖”和“饭团”,它们的配送车上印有拟人化的饺子标志,在街头很常见,就像其他美国大学城的红蓝色达美乐披萨车一样。
“司机都是中国人,”钱女士说,“他们到公寓后,会打电话给我,直接说普通话。”